当结束成为动词,疫情消散于日常的褶皱中
凌晨三点,外卖骑手的电动车碾过潮湿的街道;清晨七点,地铁站里响起熟悉的报站声;午后两点,会议室里有人为方案争执,唾沫星子在阳光里飞舞——在这些不被标注的瞬间,疫情正从我们的集体意识里悄然退场,它并非在某场新闻发布会上被庄严宣告终结,而是像退潮般,一层层剥离我们的生活,最终只留下被冲刷过的、崭新的日常地貌。

回望来路,我们曾无比渴望一个确切的“句号”,2020年初,我们以为那会是一个闷热夏天的结束;疫苗问世时,我们期待免疫屏障筑起之日;病毒不断变异,我们又寄望于某个特效药或某个神秘的时间阈值,疫情结束的方式,与它暴发时雷霆万钧的登场截然相反,它没有“轰然”的巨响,只有“渐然”的消逝,结束的,首先不是病毒本身——它或许已演变为季节性的背景音——而是那种高度紧绷的“战时状态”,健康码从每日必查变为偶然想起的旧物;核酸检测亭在某个清晨悄然变身为早餐铺;深植于心的社交距离,在久别重逢的拥抱里融化,结束是一种感觉,是某天你突然发现,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下意识地去摸口袋里的口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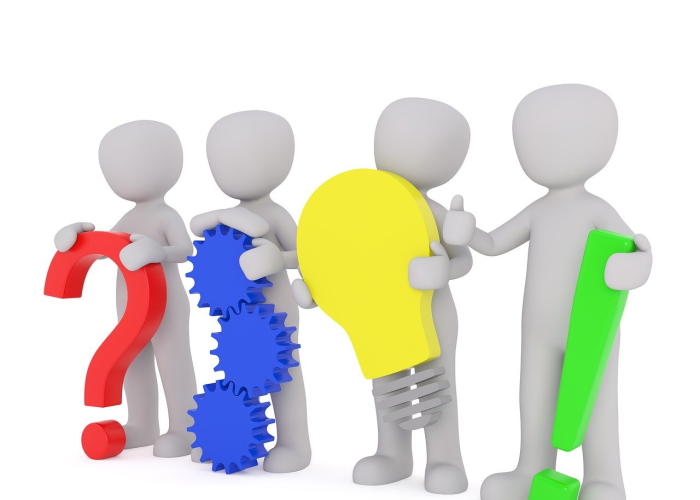
这悄然的退场,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孤例,1918年大流感,没有全球性的终战宣言,它在第三波高峰后逐渐力竭,融入了普通流感的序列,黑死病席卷欧洲后,其终结也非一纸诏书,而是人口结构、卫生习惯和社会形态被彻底重塑后的“新常态”,历史的经验暗示我们,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终结,往往不是一个医学问题,而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,当恐惧让位于疲惫,当特殊沉淀为日常,当全球绝大多数人已在心理和行为上接受了与病毒共存的模式,结束的时刻便已降临。
疫情真正的“结束”,发生在我们重建“附近”与“当下”的能力复苏之时,它结束于街角咖啡馆再次坐满闲聊的陌生人,结束于孩子能毫无顾忌地触摸游乐场的沙土,结束于我们敢于为遥远的未来制定计划,结束于我们重新获得为眼前琐事烦恼的奢侈,这是一种集体认知的迁徙:我们从“紧急的幸存者”,回归为“平凡的生活者”。
疫情没有在某个被载入史册的日期“结束”,而是将“结束”本身,变成了一种持续进行的状态,它是一个动词,而非一个名词,我们并非站在终点回望,而是携带着这段记忆,持续地走进一片被深刻改变、却又顽强地焕发生机的土地,海平面已经改变,而我们在新的岸上,学习呼吸。







![[玩家实测科技]“欢聚水鱼虎步龙行开挂器”[必胜开挂神器] [玩家实测科技]“欢聚水鱼虎步龙行开挂器”[必胜开挂神器]](https://shop.weiyanzm.cn/zb_users/cache/thumbs/8ac4dd140046316768b2d198e8d712f9-300-200-1.jpg)

发表评论